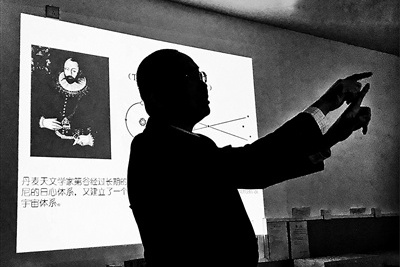
在京生活多年,一次次走过古城西南角的古观象台,心中每感神秘庄严。那拔地而起的灰色砖砌建筑,显得自有风范与众不同,与周围林立的现代化建筑相比,更有难以言喻的历史沧桑之感。
始建于1442年的北京古观象台,作为明、清两个朝代的皇家天文台,至今已有575年的历史,是明、清两个朝代引进西方天文学的历史见证。在这座观象台的附近,元代郭守敬曾经修建过“大都司天台”,那时建国门一带叫做“都邑东墉下”,明朝称观天象的台子为观星台。
2017年12月24日,又一个寒冷晴朗、有风的冬日,北京青年报“青睐”三十位忠实铁粉,难掩期待已久的热情,如约来到位于建国门东裱褙胡同2号的北京古观象台。在这里,他们得以和五百年前的钦天监官员一样,与代表中国铸造工艺最高水准的清代铜制天文仪器零距离接触。现场还有大人带着孩子,不拒寒风细细观赏,试图参透古仪观天的原理。进而又听古观象台常务副台长肖军介绍古观象台的历史,从徐光启的《崇祯历书》谈起,讲到柏拉图“拯救现象”背后的故事与西方科学的关系,感叹500年前先人以仪象天的智慧与巧夺天工的技艺。
古观象台的前世今生
北京古观象台及其附属建筑群的规模和格局,在明代就已确立。1644年清人入关建立政权之后,全盘接受了包括观象台在内的明代皇家建筑,观象山继续担当皇家天文观测之责。
明清时期,观象台的东侧与城墙相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墙被拆除,现仅存观象台。观象台西侧有紫微殿、晷景堂等附属建筑。紫微殿坐北朝南,左侧安放的是明代的浑仪,右侧是简仪。殿内悬挂着乾隆皇帝题写的巨匾,上书“观象授时”,四个字精准概括了古观象台的职能: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据以制定和颁布历书。匾下立柱题联:“顺敷星好敕时几,敬协天行所无逸”。东西配房辟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展览”展室。院内古树参天,安放着历代著名科学家张衡、祖冲之、沈括、郭守敬、徐光启等的半身铜像。这些雕塑静静伫立,仿佛能引我们沿着时光逆流而上,开启他们背后一个个艰苦卓绝的探索故事。
古观象台高14米,坚实的方形底座,最初台基用黄土夯筑,四周砌砖。现在台体采用了空心结构,并开辟为展览厅。沿着北侧台阶拾级而上,我们在肖军副台长的带领下来到观象台顶。台顶南北长20.4米,东西长23.9米,五百年间这里不知留下了多少人观测天象、探索宇宙的足迹。每年农历十月初一,皇帝在午门举行颁朔大典,颁布次年历书。庄重肃穆的典礼背后,凝聚着钦天监官员风雨无阻、日日观测的辛劳。
件件精美的天文仪器,屹立于苍穹之下,似在无声诉说尘封的往事。其中五架仪器1900年曾被德国侵略者掠至德国,1921年归还中国,被重新安置在古观象台上。镶嵌1888颗镀金铜星的天体仪球面上,至今留有当日德国侵略者的弹痕。饰有盘龙纹的象限仪;还有测量任意天体角度、广泛应用于航海、完全西化的纪限仪,更有历经十年铸就的玑衡抚辰仪,无不展现明清时期科学达人们的智慧和精巧技艺。仪器的底座和边缘装饰着云朵和龙形图案。龙是生命的图腾,代表生生不息。
观天仪器皆体形巨大、造型优美、纹饰精湛,历经沧桑辗转流离,如今能够存留于世供后人欣赏参观,已属万幸。八架仪器当中的六架——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天体仪、地平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是清康熙八年(1669年)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奉康熙帝之命在前人基础上设计,至康熙十二(1673年)年制成。新仪制成后,明代仪器被全部移放台下,新制六仪安于台上用于观测。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德国耶稣会传教士纪理安设计的地平经纬仪制成,是地平经仪和象限仪的合成,使用起来愈加方便。玑衡抚辰仪是为古观象台制造的最后一架大型观测仪器,当日乾隆下令铸造并亲自命名,历时十年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完成,重达5吨,由青铜浇筑,设计巧妙,制作精美,几条游龙栩栩如生,气魄宏伟,为我国天文文物之瑰宝。
古观象台,明清两个朝代一直承载皇家天文台的职责,从事连续天文观测活动。之后,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经由天主教传教士传入中国,钦天监改用欧洲天文学的方法编制历书,并按新计量制度铸造了八架新天文仪器,它们体现了当日天文仪器的最高水平,也代表着中国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准。

1610年,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天文开创了近代天文学,所以北京古观象台这些仪器是没有安装望远镜的最后一批古典天文仪器。它们不仅用于观测天体和天象,还有一个象天的功能,即通过仪器的结构来模拟天象与天道,这是望远镜所没有的功能。中国传统有一句话——“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就是说天是有道的,通过这些仪器上的黄道、赤道,可以看出天体的运行是有规律可循的。
徐光启和《崇祯历书》:没有徐光启就没有今天的历法
徐光启在明朝末年主持历局聘请欧洲传教士编译《崇祯历书》,标志着欧洲古典天文学被吸收和传入中国。
《崇祯历书》以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为主,在推算日月行星运行时,没有继续沿用中国传统的代数方法,而是引用了欧洲古典天文学中的几何模型方法,对中国历法是一次巨大的变革。从此将古希腊天文学家创立的行星运动的轨道模式,引入了中国,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宇宙观,是中西天文学交流的第一部巨著。
上世纪九十年代,肖军参与中国天文学史大系项目,编纂《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中有关《崇祯历书》的章节,从而对《崇祯历书》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徐光启这一历史人物也有了初步的认识。
中国人的宇宙观与西方人的宇宙观,两者有什么不同?中国引进西方天文学,徐光启的历史作用是什么?在历书当中东西方的智慧是不是都有所体现?和我们现代的天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带着上述这些问题,我们随肖军台长重新认识徐光启。
徐光启的突出贡献,在于跟着利玛窦完成了西方科学名著《几何原本》的翻译。利玛窦刚完成《几何原本》上半部有关平面几何的部分就去世了。《崇祯历书》还没有编完,徐光启也去世了。可以说他们穷极一生,完成了西方科学进入中国的基础铺垫,为西学东渐打开了认知之门。
几何学是西方先哲的一把量天尺。要想研究宇宙,必须了解几何学。几何学的空间构架,是西方科学的基础学科,可以上推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徐光启认为它是“以不用为用,众用所基”,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
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说,中国历来是“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就是说我把鸳鸯绣出来给你看,但我不把绣鸳鸯的这个针给你——相比较工具来讲,我们更重视成果。而徐光启借用这句话,反过来说“金针借去从君用,不把鸳鸯度与人”。引进《几何原本》,引入的是现代诠释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模式,相当于一把绣出鸳鸯的金针,也就是中国人常言之“授人以渔”的“渔”。

天文历法是古代帝王最核心的统治依据。以当日的生产力水平,天子受命于天,天机不可泄露,谁掌握了“观象授时”谁就能掌握统治权。换言之,在当时以农、牧、渔为主的经济活动中,天文历法就是最核心的生产力要素。改朝换代一开始要做的就是修订历法,通过修正历法以顺承天时,借此名正言顺地统治天下。
徐光启在编修《崇祯历书》之初,提出了“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改历方针,并做了三个层次的工作。首先,他通过一次准确的日食预报,用成功案例说服了当时的崇祯皇帝采纳西学编制历法。其次他完善了编制历法的结构,按照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排列出来,实际上之后的《崇祯历书》就是以这样一个结构模型完成的。第三,他认为还应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要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当时欧洲的宇宙模型,有地心说、日心说和第谷折中学说。跟张衡一个年代的托勒玫地心说显然更受宗教的欢迎,而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当时的常识水平下让人难以接受,最终实测天文学家第谷设计的一个折中地心和日心的宇宙模型,被朝廷认可成为钦定的宇宙模型,被《崇祯历书》采用。
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说,各种学说思想传入时,都有一个学习接受的过程,这种几何模型式的宇宙观在那个年代,还无法真正影响中国大多数人的传统宇宙观和思想。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整个近两千年的天文学历史,《崇祯历书》在短时间内做了一个汇聚,将之引入中国。如何真正地来认识这套东西,还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如此看来,重新认识这段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有助于我们认清自身的文化传统。

科学的原问题:柏拉图的洞穴之喻,透过现象发现本质
数理天文学,用数理模型构架宇宙这件事,实际上要解决的是行星运行的不规则性。为什么会有顺逆行现象?柏拉图认为有一个真相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他让他的学生用匀速圆周运动来解释行星的实际运行,后来他的学生阿波罗尼( Apollonius,公元前262~前190年)在公元前220年设想出了一套本轮均轮的几何模型来解释行星的运动。这一方法整整用了两千年,一直用到开普勒方才结束,这就是柏拉图著名的拯救现象问题,整个西方天文学的构架,就是在这样的原问题下构架出来的,它的科学理论、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都在这套东西里面形成了。
而原问题并不一定是所谓对的问题。经过两千年的探索,最后发现柏拉图的匀速圆周运动想法是不对的,但是为了拯救行星的不规则运行而构建的几何模型的数理方法,孕育了西方科学。科学传播到中国,有时被神化了,成了绝对正确的代名词。从科学史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科学的实际。我们今天讲的原问题,在科学史中,有带动连环的效应,最后构造了具有传统的西方科学体系。所谓对现象和现象背面真相的认识,这样的一套思想的架构才是核心。
柏拉图有一个洞穴之喻。就像在一个洞穴里生起一把火,人在火前跳舞,人跳舞的影子投射到洞的墙壁上,他认为我们这些凡夫是面冲着这个墙壁坐着,我们看不到身后的人在火前跳舞,我们只看到了影子。他认为我们见到的现象世界,都是洞穴上的这些影子,他认为在影子的背后有一个真相,真相的世界是完美的,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虚幻的,变换无常的。我们要通过变化的现象世界去寻找背后的真相世界,这是他的思想。简单地说,你画一个圆,实际上你怎么画都不对,都不是完美的圆。他说几何学里的这个圆才是理想世界的圆,理想的世界才是真相的世界。你头脑里的圆比所有现实的圆都要圆,世界上所有存在的圆都不圆,只有你头脑中那个圆才是圆。他认为那个东西是真的,你看到的都是假的,所以他要找那个真的。所以在宇宙现象的背后,他要找那个真相,于是就提出了那个问题,说行星的不规则运动需要拯救,你只有用匀速圆周运动把它给拯救了,宇宙的真相才是我们的智慧可以接受的。
中国人的宇宙观,讲究的是天与地的和谐
接触西方这套宇宙观之后,我们开始时仍是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等我们了解了科学史的原问题之后,禁不住要问,中国天文学有没有这样的原问题?
中国传统天文学有一件事,就是要寻“中”。在河南登封告成镇有郭守敬做的高表,还有“昔者周公测晷影于阳城,以参考历纪”的说法,周公曾在此地立竿测影,唐朝723年仿周公旧制建了现存的周公测影台,目的都是在寻“中”。如周礼上所说,“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它的方法是在夏至的时候,用圭表测得日影长一尺五寸的地方就是地中,用立竿测影的方法来寻“中”。
现在大家知道地球是圆的,根本没有地中。现存最早的立竿测影仪器是秦汉时期的晷仪,这个仪器实际上是用来观测太阳一年四季升落方位的变化。这架仪器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写的“中”字,是平面的书写,实际上晷仪是“中”字的三维立体表现,在四方的盘面中心立一根杆子。所以晷仪亦可称为中仪,什么是“中”,古人在寻“中”的过程中得到了什么,这个是需要我们重新去看的。
700多年前,元代郭守敬在河南登封观星台,利用创制的天文仪器,经过几年辛勤观测和推算,编制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授时历》求得的回归年周期为365.2425日,合365天5时49分12秒,与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使用的阳历——格里高里历,一秒不差,但格里历是1528年由罗马教皇改革的历法,比《授时历》晚三百年。换言之,我国在元代的天文历法就在世界天文学中处于领先地位。
西方天文学的模式是什么?它是上帝的视角,站在宇宙的外面看,从日心体系到现在的宇宙大爆炸,都是站在天的外面看。我们中国人的模式,人是站在天地之间,仰观俯察,正如易经所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天和人有关系,天和地有关系,天和地是不能分开的。伏羲和女娲,一个拿规,一个拿矩;一个画方一个画圆。天道曰圆,地道曰方,中国人追求的是道。
海德格尔看到人类登月之后传回来在月面上看地球的照片,说了一句话——“人类将失去大地的意义”。他洞见到人类如果没有了大地,失去了大地的承载,就会开始感受到不安。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我们传统天文学的理念,是要恢复大地的意义。跑得再远,如果没有了大地的标准,对于人类来讲,就会失去方向。中国人讲天为父地为母,大地是允许你摔跟头的,母亲如果不允许失败,这孩子是不会有出息的。所以对中国人来讲,缺了大地是不行的,我们讲究的是天和地的和谐统一。
现场问答
提问:很好奇汤若望这个人,他是最后完成《崇祯历书》的人,如今在观象台西配殿紫微殿边上还保留有他的办公室,他和咱们古观象台有什么关系?对我国传统观星术有什么看法吗?
肖军:汤若望是徐光启请来做《崇祯历书》的。那个时候是金尼阁第二次来中国,他挑了7000多本西方经典著作带来,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编译《崇祯历书》时用到的开普勒、哥白尼的书,实际上都是金尼阁那时候带进来的。他带书的同时还带了人,不只汤若望,还有罗雅谷等一批传教士进来。徐光启把汤若望从西安邀请到北京,为的是编《崇祯历书》。
汤若望为什么起的作用比较大?一个是在《崇祯历书》里他负责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还有一个很关键,明朝灭亡之后多尔衮让汉人和外族都搬离北京内城,那时候汤若望的那些书、天文仪器都在南堂,如果全搬出去的话肯定会有遗失或损坏。为了保住这些东西,汤若望当时就给清廷上奏折,说他要敬献历法。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一次改朝换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颁布历法——首先要把天地的秩序排列出来。不能制定历法,说明你的权力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对于满人来讲,汤若望确实帮了大忙,他把这部历法敬献给清廷,清廷就采用了。1644年颁行这部历法,《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算书》。就是在改朝换代期间,汤若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顺治很尊重他。
顺治去世后,汤若望开始走背字,几次被人告“谋反”,最后判他凌迟处死。宣判之前出现彗星,宣判之后北京五次地震,最后是顺治的母亲孝庄文皇太后救了他,免他死罪。第二年他就在北堂去世了。
汤若望在中国,他人生的后半段荣辱都受了。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开始中国人接受西方这些东西还是有阻力的,包括他的学生南怀仁做天文仪器都和他有关系,南怀仁到康熙朝给他平反,最后到康熙时重新用西学,其实都跟他有关系。所以他是西学东渐的关键人物。本版文/荆洲 摄影/溪哥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00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003号